4月8日下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应我系邀请,在珠海校区教学楼C305作了题为“大数据时代的深度学习:以明清小说中有关香料与白银的叙事为例”的讲座。本次讲座由陈春声教授主持,刘志伟教授、吴滔教授、于薇教授出席。
讲座伊始,黄一农教授由红楼梦研究引出大数据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冲击——在大数据时代,海量文献以更为便捷的方式呈现,要求研究者本人进行思维方式的创新。随后,黄一农教授以白银为切入,从“宝玉祭金钏”的情节出发,考察明清时期白银的实际行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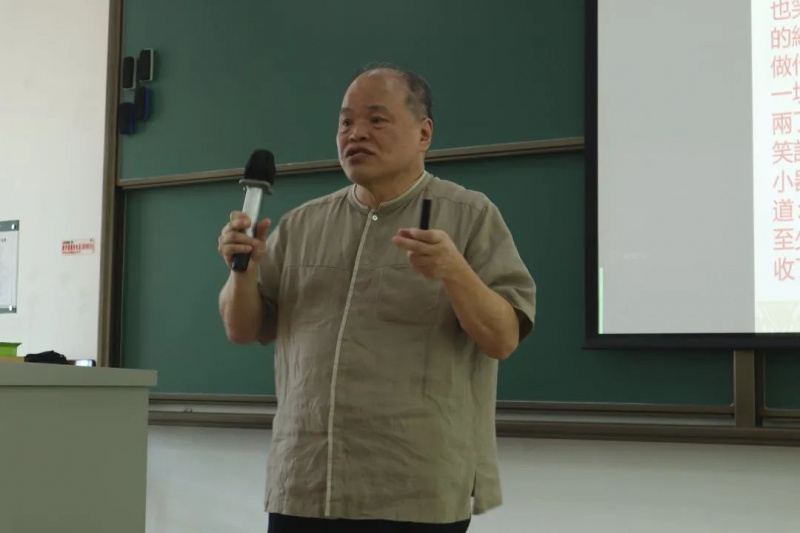
一、 《红楼梦》中的“沉、速”
黄一农教授提出《红楼梦》中“沉、速”是两种特殊香料。在“宝玉祭金钏”的故事中,贾宝玉曾用“两星沉速”拜祭金钏,但目前各种《红楼梦》注释本并未对此有过明确解释。通过大数据的检索,发现明末《度支奏议》中有载“沉、速二香产自海外,购之稍难”,这说明不是一种香叫沉速香,它是沉香跟速香。又据《香乘》所述沉香与速香等比例混合,添加其他原料后,可制成沉速棒香。这两种香的区别在于,“沉香置水则沉,半沉者为栈香,不沉者为速香”(见《本草纲目》)。
二、《红楼梦》中的“两星”
黄一农教授认为《红楼梦》中的“两星”就是两钱的含义。作为量词的“星”,不仅用于香料的计重,也常用于称重银两。在明清小说叙事中,多次出现用银若干星的语句。其中,《笑林广记》有言“有人遇喜事,一友封分金一星往贺,乃密书,封内云:现五分,赊五分”。由此印证出“星”即“钱”的含义,“两星”即“两钱”,表示物体重量。
三、 中国古代的戥子
黄一农教授介绍了中国古代戥子的形制和用法。同样是在《红楼梦》中,袭人和宝玉在向太医支付酬劳时,使用戥子称量银两时,袭人问道“那是一两的星儿?”通常而言,戥子是用来秤金银、药材、香料等名贵物品。使用时,秤砣在刻度上移动,来称量物品的实际重量。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中国古代的戥子制作并未标准化,形制各异,也易出现市场欺诈行为。其中,“星儿”意指戥子较大的刻度。
四、 明清时期白银的使用
黄一农教授讲授了明清时期白银实际使用情况。明清时期,国家并未铸行银币,市场以称量银作为货币。民间不仅需戥子称量白银,还要裁剪、熔铸白银。其中,挟剪除用来产生合适交易之碎银(若有差额,则以制钱补足)外,另一目的则是要从被剪开的截面来判断银锭有无掺假。用挟剪处理较大银锭时,得要加上身体重量方可,由于银块不大,且形状往往不规则,剪时若用力过猛,容易打滑,故不掌握窍门就易受伤。
熔铸则是将细碎银两熔化,重铸成高品质白银,用于高消费。明代《醒世恒言》中有着详实描述:卖油郎先是贩油积攒细碎银两,凑到一定程度时,再折换成较大银块;而后,前往倾销店称量白银,而后在熔铸成高品质的大银锭;最后再持这些银锭进行高消费。
各地常用银有着不同成色。例如成色较高的白银,一般银锭底部有蜂窝状或水丝状,称为“细丝银”。再如云银(即系肚银),九七成色起,至七八成色不等,干银则是97%以上成色的白银。若是以“干银”检索则会发现有2000多条“干银”。
形色各异的白银也易引起市场纷争。不同成色的称量银要求双方娴熟掌握白银鉴别知识和技术。为此,市场交易发展出两种途径尽量杜绝因白银成色造成市场欺诈行为:一是,银锭熔铸过程中铸上特定印记,据银两收藏家吴宗喆告知,银锭上的单槽、双槽、三槽等乃指锭面打印的凹槽数目,而《新刊辨银谱》中的“京槽”、“广槽”等词,乃指银锭上题称的倾铸处。二是,当时有大量书籍传授鉴别白银的成色的知识,如《杜骗新书》、《新刊辨银谱》等。
白银使用也深刻影响当时社会经济。其中,“低潮”和“倾销”语义的转变即是典型个案。在明清时期,“低潮”常指低成色的白银,而“倾销”则是白银熔铸,都与现代词义不同。通过对近代报纸数据检索,可知语义改变大致发生在词义之改变应发生在1920年代前后,此乃受银本位币制遭废除的影响。
五、结语:e考据与文史研究
最后,黄一农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总结,说明了大数据对文史研究的积极意义,提出e考据。传统与数字的对话与融通,将是新一代文史工作者无法逃避的挑战。e考据不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新世代文史工作者难以逃避且该用心拥抱的技艺。数字落差不仅是衡量所掌握数据库的多寡,更取决于如何能透过传统功底和逻辑思维,提出一个又一个具学术意义的问题,并统合这些问题以形成有机会成功的运作模式。接着还得善用数据库的特性,尽全力去找出可解决各个问题的论证。
讲座结束后,陈春声教授进行了总结。吴滔教授代表学系向黄一农教授赠送纪念品。整场讲座在掌声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