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重庆市学术技术(世界史学科)带头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徐松岩老师,在海琴6号A324作题为《特洛伊远征与海盗》的讲座。我系22级博士张广宇同学主持,吴滔老师出席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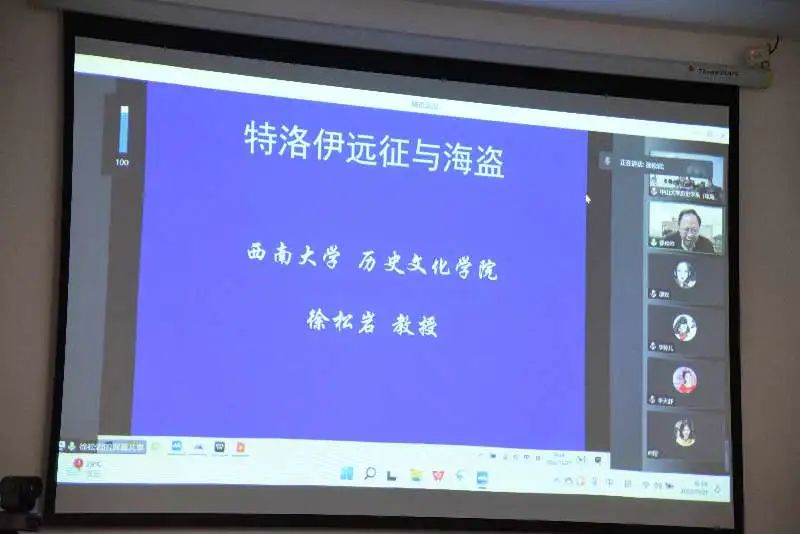
讲座伊始,徐松岩教授以爱琴海住民为切入点,指出古希腊人并不是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的原住民。爱琴海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由于新石器革命首先发生在西亚,而西亚地区伴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其主要产品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往东传播到达中国;往西传播的其中一条路线就是爱琴海。古希腊人到达爱琴海是在大约从公元前2200年以后,说希腊语的居民从北方陆续南下来到爱琴海诸岛,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而最晚的一次移民(即斯巴达人),就在特洛伊被攻陷的第八十年(特洛伊城被攻陷,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跨时代的、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徐老师指出,爱琴海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它有三千多个岛屿。这个地方是古代希腊人运粮食的要道,同古希腊关系密切。但是即使此处确实重要,在古代,海上航行耗费的时间和金钱以及安全成本都是极大的,并且爱琴海在冬天也因为风浪过大而并不适合航行。由此,徐老师引出了本次讲座的重点问题:希腊人发动特洛伊远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徐松岩教授首先给我们进行了故事主体介绍。他梳理了希腊文明的起源,明确了希腊人族源总体上是由西亚新时期时代以来文明西传和北方民族南下组成,在之后不断发展、融合。同时在这部分给出了考古学、词源学、人类学等考察证据。从语言学、词源学角度,徐松岩教授强调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的互融。对此,他提出了-ssos -ttos -inthos -enai 非希腊语词缀等语言学证据。由此他认为,爱琴海地区的文明其实是希腊人的皮拉斯基化、皮拉斯基人的希腊化的文明互鉴的结果。从人类学角度,徐教授由火葬、土葬的形式的相互影响说明了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最后得出结论:希腊人族源复杂,是多元融合后的结果。接着徐老师从使用陶器、线形文字石板、野猪獠牙头盔、城墙遗址、阿伽门农面具等造器,及更多的历史证据为我们引入了具体的历史时段——存在于公元前16到12世纪的迈锡尼文明,并提出特洛伊远征是他们最后的壮举。这就帮我们确认了故事的文明坐标和时空坐标。在这之后徐老师通过各种精巧详细的图片,为我们展示了梵蒂冈收藏拉奥孔、现代复原特洛伊木马、古城墙遗址等相关母题,展示特洛伊全城地图(平面、立体),及由吴滔老师亲自拍摄的——不同地层高度的特洛伊古城考古证据,以及其它文物线索。辅以精妙讲解,使人身临其境。总的看来,特洛伊古城的位置得天独厚,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也是东西交往的必经之路,十分富有,容易引起“强盗”的觊觎。——这实际上暗示了特洛伊是兵家必争之地,初步回答了希腊人发起特洛伊远征的原因。
简单介绍了特洛伊以及爱琴海地区文明之后,徐老师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特洛伊战争是否是希腊人发动的。徐教授首先进行了简单的学术史梳理,为我们引入、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学界相关重要议题及观点。对于这个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学界大概有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说法认为,特洛伊战争纯粹是亚洲人之间的一场战争。阿凯亚人(Achaeans,前期移民到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一支)只是参与其中。20世纪以来,麦卡锡主义和疑古风盛行。持有此说者主要有英国学者 M.I.芬利和美国学者Chester G.斯塔尔。第二种说法认为,就是希腊人毁了特洛伊。坚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教授C.W.Blegan布勒根, D.L.Page佩吉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研究学者刘健提出了赫梯文献里的阿希亚瓦问题(从时间上看,阿希亚瓦人就是阿凯尼亚人)。
接着徐老师提出,传统上,前12世纪初展开特洛伊战争的断代是值得怀疑的。在传统说法的支持下,芬利认为,在公元前1184年希腊本土遭到了普遍严重打击,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们难以在这期间发动大规模战争。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特洛伊城陷的年代。对此自古就有多种说法,如公元前1334、1270、1240、1234、1225、1212、1209、1193、1184/3、1171、1135和1129等几十种说法,其中有10种影响比较大。如果它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后期,希腊联军远征之说便可成立; 如果它发生在前12世纪初(传统说法是前1184/3年),则芬利的说法亦不无根据。因此,芬利的论证所否定的不是希腊人发动远征的可能性,而是否定了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的可能性,换言之,传统上把特洛伊城陷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2世纪初是值得怀疑的。现代学者大都把它定在公元前13世纪后期。布勒根综合考古学证据,认为特洛伊城攻陷的年代为公元前1240年。这种说法有一个有力的佐证,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罗多德(《历史》,Ⅱ.45 )提到,特洛伊城陷在他之前800年左右,而希罗多德《历史》希罗多德在前440年左右。帕罗斯碑铭文则把城陷年代定在公元前1209年。至于希罗多德的主要依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由于希腊人相当重视血统,其后裔对其祖先光辉事迹的记录应该是极其严格的。因此总的来看,徐教授肯定了传统观点——认为是希腊人在东方小亚发起的一场战争。
第二,特洛伊战争的传说最早在亚洲西部流行的原因。徐老师指出,希腊早期居民来自新时期农业革命以后的西亚北非,当年远征军后裔在特洛伊战争后,随“伊奥尼亚”移民潮移居到小亚细亚西部,因此西亚地区才是希腊文化长期沉淀和积累的地区,这是有关传说在这里流行的主要原因。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胜利者在当地成功进行殖民,遂胜利者的光辉事迹最早在被殖民当地,也就是小亚细亚地区广为流传。在这里徐松岩教授还提及了希腊诸神的阵营的问题。他提出,希腊的神分为支持希腊人(雅典娜、赫拉、波塞冬、赫尔墨斯) 支持特洛伊的(阿佛罗狄忒、阿瑞斯、阿波罗等)两拨,而宙斯处于中央。神话虽不是传统的“信史”或史实,但却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社会意识。
第三,特洛伊战争真实起因。根据《伊利亚特》记录,此次战争希腊人出动了一千一百八十多艘船,具体的数据虽然有待考察,但至少可以确定规模极其庞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战事,值得深入考察。因此这一部分是本次讲座的重点所在,在这个部分徐老师列举了学界不同说法,逐个分析、解释了这些看法,列出了许多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并给出了自身判断。第一种看法是商业竞争说。由于古代航海需要沿着海岸线走、随时看到陆地,否则找不着方向,因此海岸线长的爱琴海确实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这一说认为,希腊人是出于商业动机进攻特洛伊。这听起来貌似合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松岩教授指出,根据史实,希腊人的做法不是想跟当地人合作,也不是大量移民占领该地,而采取的是“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因此他们应该是来掠夺的而不是做买卖的。第二种说法是争夺霸权说。修昔底德提出,这其实是把古代的历史“现代化”,把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争夺海上霸权的说法和意图,简单转接到古代去。第三种是转嫁危机说。当时希腊内部确实存在危机,王位争夺、贵族争执、阶级斗争,现代国际关系中也有转嫁危机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希腊攻打特洛伊的战争并不容易,跨海作战、海上远征代价成本非常大,没有那么轻易“转嫁危机”,稍有不慎,甚至还有可能加深危机。况且如果希腊真的是出于转嫁危机的意图,那么找一个地理位置相近民族进行嫁祸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第四种,复仇抱怨说。这一说法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认为战争的起源是特洛伊拐走了斯巴达的王后——美女海伦。一般认为,这个说法可能是现实的附会、转化。神话化,神秘化是希腊人惯用的叙事手段,用来赞叹、歌颂丰功伟绩,或美化战争。而波斯人的记述认为,这其实是抢劫行为。对此,希罗多德首先提出质疑:
“他们说,劫掠妇女固然是无赖之徒的行为; 但是因此而处心积虑地进行报复,那一定是蠢人所为。明智的人是丝毫不会对这样的妇女介意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决不会被强行给劫走的。波斯人说,在希腊人拐走他们亚细亚的妇女时,亚细亚人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可那些希腊人,仅仅为了拉栖代梦的一个女子,便纠合了一支大军,入侵亚细亚,并且摧毁了普里阿摩斯的王国。
如果海伦是在特洛伊的话,那么,我认为不管亚历山大(帕里斯)同意与否,当地居民都会把她移送给希腊人的。因为可以肯定,无论是普里阿摩斯,还是他的家人,都不至于愚蠢到竟会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城市陷于危险的境地,而仅仅是为了亚历山大能够拥有海伦。假若他们在一开始决定不交出海伦的话,而后来随着如此众多的特洛伊人在与希腊人历次交锋中阵亡,而且普里阿摩斯本人在每次战斗中,都要失去一个儿子,有时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我坚信,即便海伦是普里阿摩斯自己的妻子,他也会把她拱手让出的。
不仅如此,尽管普里阿摩斯年事已高,亚历山大(帕里斯)似乎并不是王位继承者,……这样的一个人是赫克托尔,他是亚历山大的兄长,而且远比他勇武,……有望在普里阿摩斯死后继承王位。赫克托尔也是决不会赞成他兄弟的不义之举的,特别是当这种行为给赫克托尔本人和其他特洛伊人带来的是可怕的灾难的时候。但是,事实上特洛伊人那里并没有海伦可以交出,他们是这样告诉希腊人的,但是希腊人并不相信他们所说……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希罗多德的论述里,特洛伊可能根本没有女人可以交出,而希腊人为了挑起争端故作不知。徐教授指出,很大程度上,那个时代的女人都是抢来的。直到后来古典时代才成为财产的一部分而得以进入家庭。
徐松岩教授表示,综上看来,希腊人的殖民欲望使向外扩张成风,或许才是其根本动机。
第四,对希腊军队的真实兵力的考证。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说法上认为,希腊联军派出了1180条战船、10万大军,平均每条船85人。然而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而得出这个数据的修昔底德犯下了一个失误——历史“现代化”。因而徐老师指出,想要更接近距修昔底德800多年前的船队,就要看更早的历史记载。例如距特洛伊战争约一百多年的Thera(传统中的西大岛)的壁画之船(Atlantis)和Theseus(提秀斯,据说其儿子曾参与特洛伊战争)勇闯克里特的返航之船,都是约为每船30桨。结合以上资料,徐老师给出看法:希腊远征军的规模大约是船均40人,总人数不足5万。
第五,特洛伊远征与海盗的联系。徐松岩教授指出,特洛伊远征事实上是地中海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海盗行为。对于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希腊人来说,暴力掠夺是他们所崇尚的事业,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在公元前4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还把海盗劫掠与农作、游牧、渔捞和狩猎并列为人类五种谋生方式之一。特洛伊战争是迈锡尼时代末期希腊人海上劫掠活动的组成部分,对于参与远征的希腊人来说,这是英雄的壮举,是值得纪念和自豪的。在一个以掠夺为荣,以战争为业的时代,在一个“英雄”与“强盗”没有区别的时代,发动战争根本无需正当理由,或者说,任何理由都是正当理由。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古典时期的海盗行为?事实上,在英雄时代,海盗行为和农耕、游牧一样,甚至是更高贵的,更值得尊重的。既是强盗行为、又是英雄行为(也是一种扶贫行为,对本地贫困户的一种助困疏解活动)。而它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塑造,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动力之一。

讲座结束后,吴滔老师、主持人张广宇同学、在场观众对徐老师表示感谢,并作出简要总结。在场同学、教师踊跃提问,并邀请徐老师再次莅临讲座。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